 学院新闻
学院新闻

2013年对于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李松而言,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在他来到北大的第十个年头,北大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在全国学科评估中拔得头筹;而他所主持的国家艺术学科重点项目“中国道教美术史研究”积十年之功,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中国道教美术史》(第一卷)出版,为他多年致力于宗教美术研究写下了又一个注脚。
艺术史研究,尤其是宗教艺术研究,是一门看似浪漫、自由,实则艰辛、寂寞甚至枯燥的学问;作为一个学科,又正受到来自诸如考古学、哲学、文学等学科的“入侵”与影响,新材料、新方法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李松用他一贯的执着、严谨、求真,在仙云艺海中拨开迷雾,探索真知,走出一条独具魅力的艺术史研究之路。

李松
走近宗教艺术——古都的感召
1986年,李松负笈西安,攻读美术史论的硕士学位。古都西安独特的文化氛围,促成了他对宗教艺术的兴趣。尽管已是20余年前的往事,李松仍能清楚地把学校周边的景致一一道来,“西安美院原来位于终南山下的樊川东岸,抬头就能看见雄伟的终南山及连成一片的秦岭。师生们散步的地方,出校门就是农田,远一点有古塔。校址所在地原为始建于初唐的兴国寺,是著名的樊川八大寺之一,至今还有两棵数人合抱的千年古树。学校南面毗邻建有玄奘灵骨塔的兴教寺,北面紧挨华严宗的发祥地华严寺,其地遗有杜顺禅师塔。越过长安县城再向北就是著名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向西有净土宗的祖庭香积寺,遗有善导塔;还有供奉鸠摩罗什舍利塔的草堂寺。”被这样一批声名显赫的名刹古塔包围,没有人能忽视宗教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对心灵的感召。李松就这样“近乎强制性”地选择了宗教美术史作为终身的志业。
就读硕士的第一学期,李松获得了一次从西安经敦煌到新疆的喀什实地考察“丝绸之路”的机会,撰写了4万字的论文《陕西石窟艺术论》,其中一部分还以《陕西关中石窟的艺术演变》为题分两期在当年的《美术》上连载。这份杂志当时是美术界唯一的权威杂志,这种少见的连载做法让李松备受鼓舞。文章发表时,为了与一位笔名李松的前辈相区别,他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李凇”。
长安这座古都,给了李松的学术研究格外丰厚的滋养。此后,李松以西安及其附近为中心,以佛教、道教为主线,兼及其他宗教,开展了一系列宗教美术史研究,论文集结成《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一书。其中,与日本著名美术史专家曾布宽川商榷唐代造像中阿弥陀佛身份认定问题的论文《论唐代阿弥陀佛的否定问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论文奖评选中获得了最高奖。“李凇”这个笔名也从当年的“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中国宗教美术研究中一个颇具分量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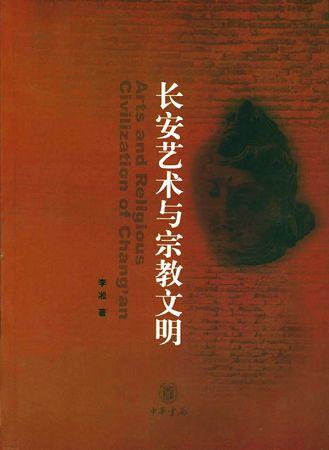
专著《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
道教美术史:曾被遮蔽的仙云玉宇
道教是中国独有的本土宗教,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创造了独特的道教文化,也衍生了大量的道教美术品。从道场到书斋,从壁画到石刻,从神仙图到圣哲像,可谓洋洋大观。但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道教美术在很长的时间内并不为人所重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由日本学者的研究发端,逐渐从佛教艺术的遮蔽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日本人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书成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中文译本1926 年出版,第十章“南北朝”内便列有“道教像””一段。大村西崖后来又做《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将道教雕塑列为与佛教雕塑相等的重要内容。另一位日本学者松原三郎的工作更为细致,在《中国佛教雕刻史论》中继续将道教雕塑单独列出,主要收入流入日、美的北魏至唐代道教雕刻。正是在美术史专家将目光转向道教时,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关注道教思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地山、傅勤家对道教和道家思想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对道教美术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道教美术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李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艺术领域。博士期间,在寻找新的着眼点的过程中,李松将注意力转向了“佛”之前中国的第一神像——西王母,使他的研究兴趣从佛教艺术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在研究中,他对道教艺术有了更多的涉猎,“半只脚已经踏入了道教艺术史”。李松发现道教美术史极富学术价值,但相关的研究却几近空白,关注的人很少,已有的成果不少存在着行文粗糙、硬伤充斥的问题。
2000年以后,陕西关中一带陆续出土了一批北朝至隋的道教造像,带有鲜明的佛道糅合的特点,进一步引发了李松的研究兴趣。他决定从小题目出发,开始着手进行道教美术的研究。几年间,陆续撰写了《三宝与五圣:唐代道教石窟及殿堂的主像构成》,《唐代道教美术年表》,《论山西龙山石窟开凿于唐代贞元年间》等一系列论文。其中,《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一文,获得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国家最高美术奖项)。
2003年,李松承担了全国艺术科学重点项目“中国道教美术史”,承接了撰写通史这样预设和目标都很大的任务。李松将整部道教美术史拆分成三个历史分期,分别为先秦至隋,唐代至宋代(含辽、金、西夏)和元代至清代。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分期,除了三卷本可以在内容上可以相对平衡之外,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中国道教美术从产生到成熟至变异的发展过程。与以往美术通史的写作方式不同,《中国道教美术史》在总体上以时间为经,以材料为纬,以具体作品及个案为中心而非以概念范畴为中心。编排时尽量显示出其完整性、独立性,如一个石窟、一座道观,其下再以自然状态和逻辑关联作切分( 如某个大殿) ,而不是简单按照视觉形式作切分( 壁画和雕塑分作两处) 。论述时也尽量考虑到其整体性和相互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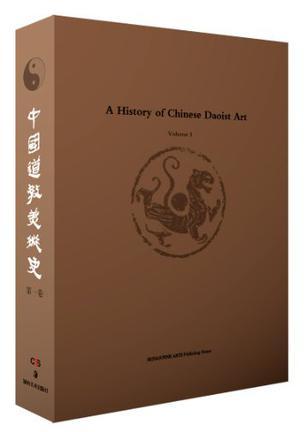
《中国道教美术史》(第一卷)
尽管时间非常紧迫,李松仍然坚持细致、严谨、深入的风格,并且坚持个人写作。从搜集原始资料到梳理学术史再到提出创建、落笔成文,第一卷的撰写就花了十年的功夫。通过一个个个案,具体地呈现了从战国时代先民升仙驱鬼思想中萌发出的前道教美术,到南北朝至隋在佛教的刺激和影响下道教美术缓慢发展的过程。这部专著的完成,填补了目前国内道教美术史研究的空白。
实地、实证——一种艺术史研究的学风
无论从事世俗艺术还是宗教艺术研究,无论是写作宏大叙事的通史还是从小处着眼阐精发微,“实地”、“实证”的学风始终是李松身上一个鲜明的特点。这既是艺术史这门学科的基本要求,也与李松求学和研究生涯中的体会与积累密不可分。
美术史是以视觉材料为核心的学科,实地考察无疑是最重要的搜集、鉴别和研究材料的途径,只有亲身实地考察,才能避免对材料认识的偏颇、片面和误解。李松每做一次研究,总要伴随着一次或者数次不辍的考察,而躬行践履也给他带来了忠实的回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松为撰写《唐太宗建七寺之诏与彬县大佛寺的开凿》,亲自去彬县做了多次实地考察。彬县大佛寺是陕西最大和最重要的石窟,考察中,李松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则十分重要的唐代长篇铭文,即“武太一题记”,显示了唐太宗与该石窟的重要联系。由此李松论证了彬县大佛的特殊起源背景,并论证了具体的创建时间,而此前清代叶昌炽和今之陕西省考古所两次拉网式的题记大搜索都没有发现这个重要的长篇题记。这个发现使李松格外振奋,“由此尝到了实地仔细考察的甜头”。“实地”成为了李松学术研究的一件法宝。

李松在武当山考察
而“实证”的精神,是学生时代的美术史老师阮璞教授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记。李松提起恩师,言语中流露出敬意与怀念:“在那一辈人中, 他的敬业精神和学识文章都堪称一流,是我当时最崇拜的老师,上他的课我做笔记最认真,生怕漏掉一句话。课堂笔记至今犹存。”阮先生一生不做宏篇大论的研究,总是从细微处入手,用考据家的眼光看待艺术史的问题,做了大量对中国美术史探赜索隐、订讹辨惑的工作。阮璞先生求稳、实证的学风深深影响了李松。在研究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唯情境。李松强调,艺术史是一门史学,强调真实性、客观性、共通性,追求历史的真相,结论不应因人而异。
艺术史中,因为不了解图像的特殊来源、结构和“原境”(context),以讹传讹以致谬种流传的现象并不罕见。李松也会经常对学界出现不严谨的误读个案提出自己的批评。2008年他就曾针对太原虞弘墓考古报告中一些树图像解读出现的偏差,撰写了《从“太原番木瓜”说读图的误区》,由寒冷的太原出现繁茂的“番木瓜树”说到“三星堆伊朗人”,系统地阐释了艺术史研究的规则,表明了治学须实证的态度。
在他的新作《中国道教美术史》的撰写中,他依然秉持“实地”、“实证”的原则。足迹踏遍山西、陕西、四川、重庆、山东等多个省,还远赴美国和日本,不仅保证了材料搜集的精准确凿,还收获了不少意想不到的新材料,其中既包括沉睡在美国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库房中的石雕造像,也包括在巴山秦地偏僻山村中的古墓壁画。一些曾被学界认为已不存的材料也随着李松的研究重新浮出水面。如 “道民王伯造老子石像” 被学界视为已经不存,李松从私人收藏家黄苗子处发现了久觅不见的拓片,通过研究可以推断,这很可能是已知最早纪年道像。
其间,有收获的欢欣,也有目睹一些古迹被湮没、破坏的心酸。福地石窟是位于陕西省宜君县的一处佛教与道教并置混合的造像窟,也是现在所知中国最早有道教造像的石窟,建于西魏开国第一年。学生时代,李松曾乘一叶小舟经福地水库对石窟进行了考察,对碑刻中呈现的“一位县令解决文化冲突”的图案进行研究。时隔不久,当他为撰写论文再次前往时,石窟已不存,只能在县文化馆的库房内见到已被大卸八块的“遗体”,令他喟叹不已。因此,撰写道教美术通史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有带有了文化“抢救”的性质。作为艺术史学者,李松期盼这样的局面能够早日得到遏制和解决。
执教北大:对艺术史教育的思考
2003年,李松离开西安,受邀加盟当时还很年轻的北京大学艺术系。从美术学院来到综合性大学,李松感到在学术上有了更大的自由,也与其他学科建立了更加积极有效的对话。
建国初期,中国受苏联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将“艺术历史与理论”纳入了美术学院,以至于这门有着独立学术期待的学科,往往沦为了艺术创作的附庸。在美术学院,李松笑称自己处在“孤独与边缘状态”。来到北大,实力雄厚的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及文学等人文学科为李松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也用美术史研究中的新成果和新的方法论对其他学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随着历史研究越来越重视图像资料,历史学学者也开始邀请李松,为历史专业的学生进行“读图”的训练。
艺术学院成立后,李松出任美术系主任,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北大艺术史学科的建立和人才的培养,思考如何建设适应世界一流大学要求的艺术史专业。李松考察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的经验,发现艺术史专业多设置在综合大学内,而且往往是这些大学内非常有竞争力的“强项”而非“短板”,并且门类齐全,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相比而言,北大的艺术史专业还有一定的差距。李松在学科设置、本科生招生、人才引进等方面做了一系列设想。目前,他最关心的是引进一批有实力的青年学者,为美术系补充新鲜血液。“慢慢来,一步一步地专业化,找准定位,发挥所长。美术系的将来一定会更好。”李松说。
艺术学院还承担着传承北大美育传统的任务。李松对艺术史、美学和美育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他提倡对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进行“充分的研究”。曾经担任过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的李松,也期望能在北大建立起一座大学美术馆。规模不需大,也区别于更偏重于考古教学要求的赛克勒博物馆,通过经典的常设展与变动多样的临时展,充分展示视觉艺术和视觉文化,不仅为艺术史教学服务,也为北大的美育和文化建设服务。
眼下,李松在此前材料收集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中国道教美术史》第二、三卷的撰写;作为首席专家,他主持的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美术史”的相关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新一届博士生的录取工作正在进行,李松又发现了几个颇有潜质的好苗子。
潜心于道教美术史的研究,对于李松而言,收获的不仅是丰硕的学术成果,也有道家独特的东方智慧的浸润,在胸襟和情怀上思接千古,以老子、庄子、陶渊明等先哲为师,在为人与为学上更上层楼。一个十年划上了圆满的句点,而学海无涯,李松用他的从容谦逊,用“板凳做得十年冷”的淡定,将他的艺术史研究和教学继续推向了深入。